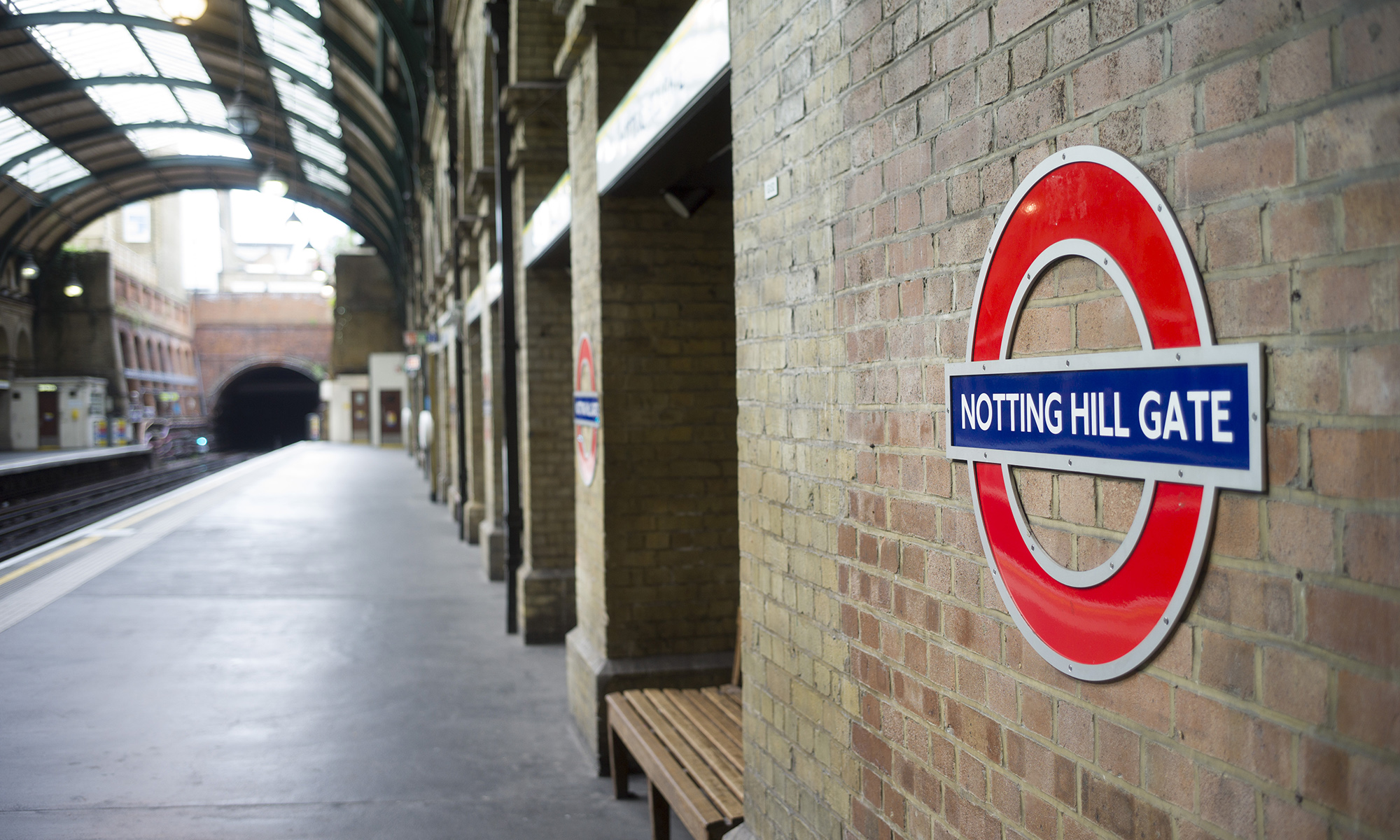紐約是一個奇怪的城巿,就像錢鍾書先生筆下的《圍城》一樣,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卻想逃出來。不同的是,錢鍾書先生隱喻婚姻及人生是圍城,而我說的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城巿。
這次回美,認識了朋友 T。本來跟 T 只有一面之緣,卻因受朋友所托,跟 T 短聚了一個晚上。T 是典型要闖進紐約的人,本來是留美學人,畢業後便決定留下來。結了婚,搞了綠咭,跟家人說以後不回港了。他在紐約教學,太太卻在華盛頓巿工作,大家相差五小時車程,但仍然認為紐約比香港好。另外,跟 P 也談了短短一杯 Latte 咖啡的時間,言談間 P 盡說紐約的好:故鄉還是老樣子,真受不了。活脫就是沈從文《邊城》倒過來寫的故事。
我了解 P 跟 T 的決定,因為我也曾經是闖進圍城的人,只不過近年所認識的紐約舊人,都是希望逃出來的較多。嚴格來說,仍然留在紐約巿大都會區的其實只有 J 吧。當年在唐人街及布碌崙流連的朋友,沒移居到史坦頓島,便是遷到新澤西洲去,有的甚至到了外州,甚至更遠的地方去。逃得最遠的應該要算到我的頭上吧,只是步我後塵的大有人在:C 辭去工作、賣掉房子後跟丈夫移居馬來西亞,外人都說 C 丈夫的 relocation package 應該很豐厚,只是 C 誓神劈願的說:一分錢搬遷福利也沒有,甚至是自願減薪,為的就是要逃離紐約。
然而,奇怪的是,短短一年後 C 又回流紐約了,朋友打趣地懷疑 C 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紐約,只是躲了在娘家一年而已。錢鍾書沒說逃出了圍城的人,會不會再想闖回去?W 姊妹分別在華埠創業,但人卻早已搬離紐約市,還要抱怨每天開著長途車上下班,回家往往已經半夜云云。G 把辦公室搬到布碌崙下城區,那裡正正就是我們年少時相識地方,舊友們早已絕跡布碌崙,但 G 卻樂於搬回舊地開創他的事業。
紐約是一個圍城,有著令人若即若離的魔力,既離不開,又靠不近。
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