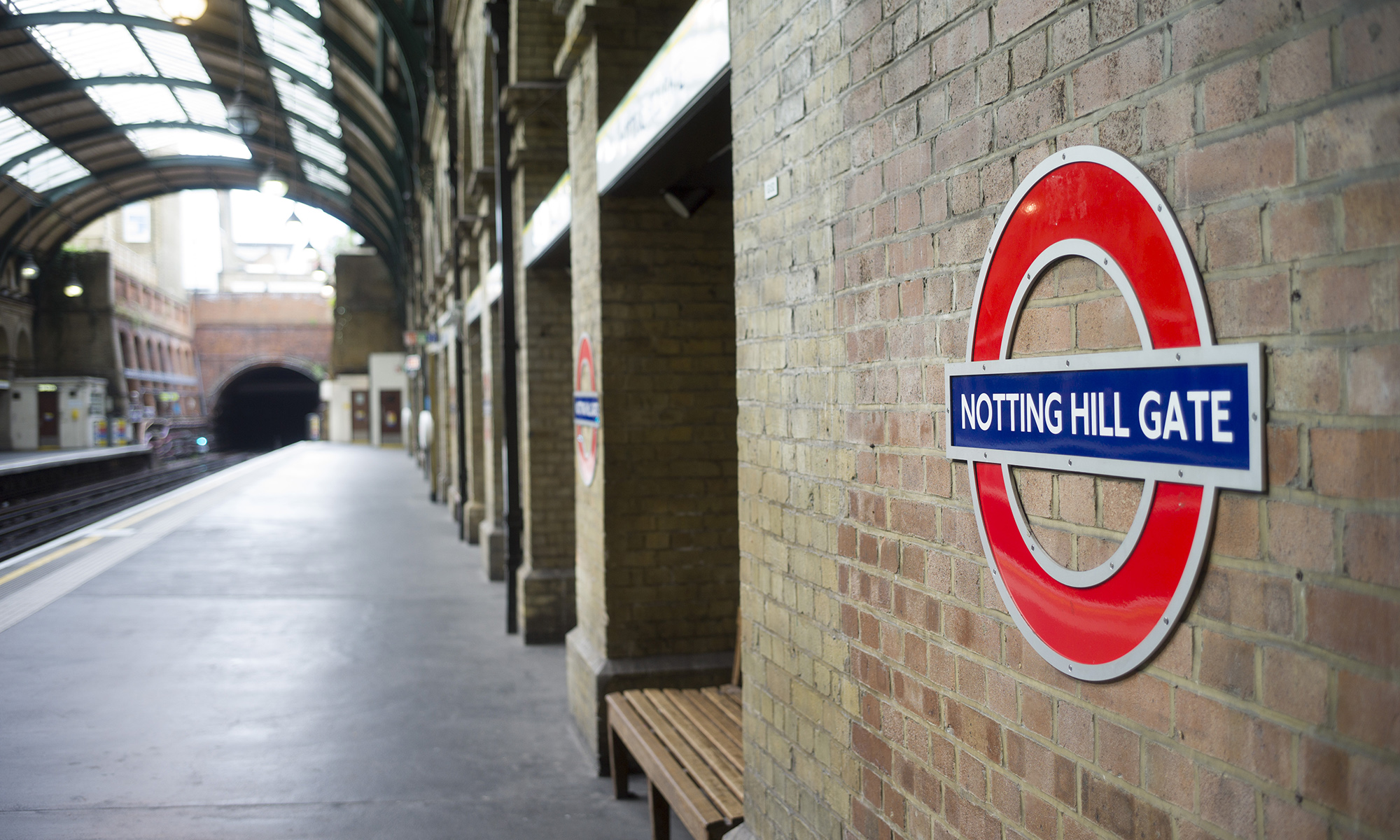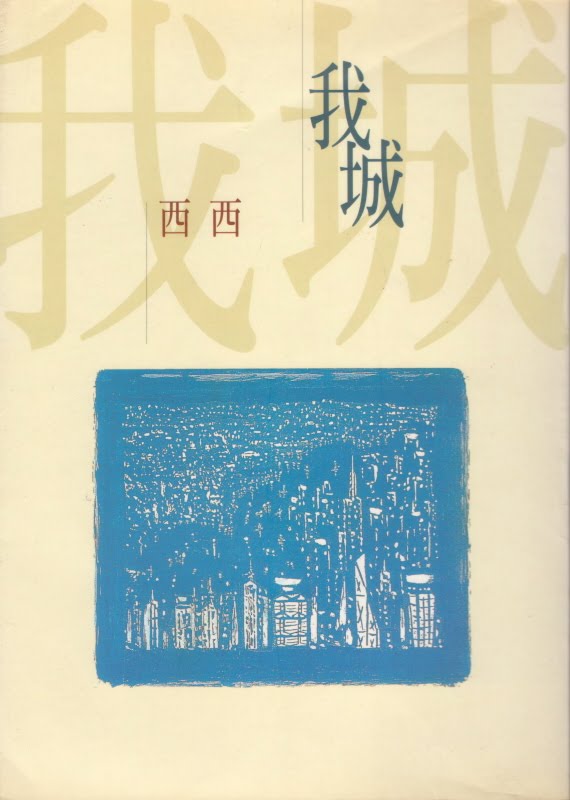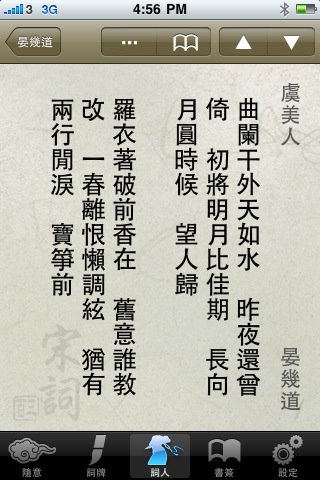這天因事要從彩虹到尖沙咀走一趟,想來想去,最方便要算是地下鐵路。前後十個車站,百無聊賴,便讀起頭上的港鐵路線圖。原來這張讀了二三十年的地鐵路線圖,當中可以讀到許多有趣的典故。這些典故源於中英文地名的差異,道出了原有地名的線索。
首先來一個簡單的 —— 調景嶺站。調景嶺的英譯音為 Tiu Keng Leng,當中『景』(Keng) 跟荔景站的 King 不一樣,原因調景嶺舊稱吊頸嶺,後輾轉改稱為調頸嶺,再後來政府開發該地,又把當中的『頸』美稱為『景』,但傳統的英譯名稱 Keng 卻保留下來,成了當初調頸嶺的線索。這個典故其實離現今不遠,在香港住上了二三十年的朋友都應該記得。另外,各位有沒有發覺調景嶺的『嶺』的英譯法跟粉嶺的『嶺』又不一樣?嶺的正音是 Ling,亦即是粉嶺站的譯法,但香港人往往把該字讀成 Leng,這個異讀音又記了在調頸嶺的英文寫法上。
另一個有趣的車站是深水埗站。深水埗站的譯名有兩個問題:第一,『埗』字讀『保』,應該譯作 Bo 才對。Po 是『埔』,亦即大埔站的譯法。原因是『埗』與『埔』、『埠』相通,古字為『步』,亦即是碼頭的意思。但廣東人喜歡把名詞的最後一個字變調,例如上述的調頸嶺↑、燒賣↑、臘腸↑(音『搶』)等等。深水『步』便被讀成了深水『保』,但原本的英譯音卻維持不變。第二個問題 —— 為什麼『深』、『水』的譯音要加上 h?本來『深』譯作 Sum 不是很好嗎?卻沒來頭被寫成了 Shum。相同譯法在上水 (Sheung Shui) 及沙田 (Sha Tin) 等地方也出現,但黄大仙的『仙』卻是 Sin,而不是 Shin。這個原因沒有可靠的典故,但有學者認為從前的居民讀 s 音都漏風,所以都要加上 h 音。這個說法沒得到證實,但黄大 Sin 卻確實不是古地名,是六十年代末才被規劃出來的地方,兩者其實沒有抵觸。
最後要說的是旺角站了。旺角英文名稱為 Mong Kok,相信無人不曉,但奇怪從來沒有人質疑旺角為什麼不是 Wong Kok?原來旺角舊稱芒角,亦稱望角,所以英國人稱之為 Mong Kok。後來望角愈來愈旺,居民便美稱為今天的旺角了,但舊英文名稱不變,令這條芒角村留下了歴史的記號。
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