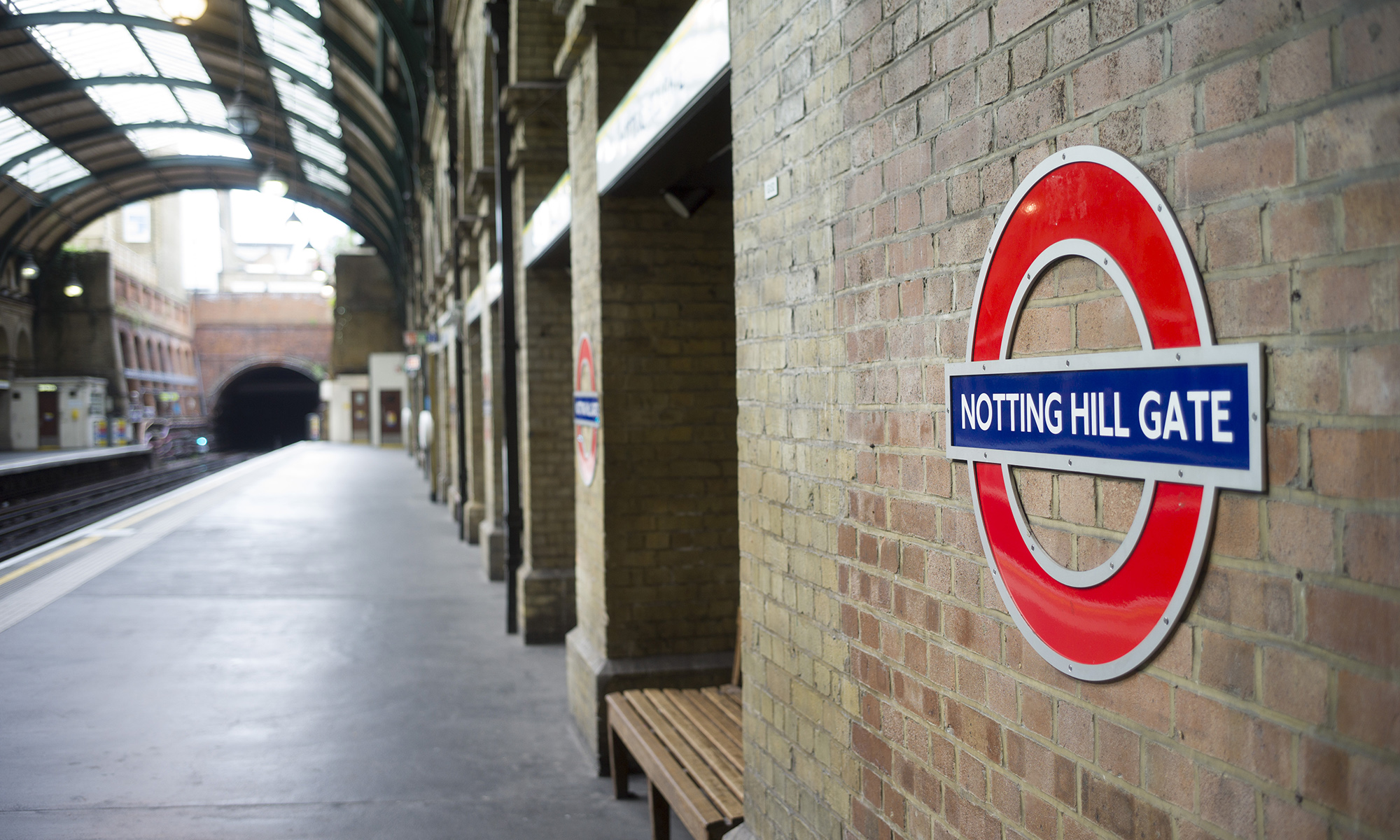這兩年變得很怕看醫生,一方面自知身體及不上從前,不外是少運動、飲食不健康、生活節奏不定時及工作過勞等都市病,然而怕看醫生的原因並非害怕他會告訴我有什麼隱疾,而是遇見過一兩位『靠嚇』醫生,令我膽戰心驚了好一會。
在美國,診所並非如便利店般方便,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醫療費,所以華人市場一般甚難經營。成功的醫生,不一定要醫術高明,而是懂得如何利用病人的醫療保險及成功說服病人來覆診。然而我在紐約最喜愛的那位醫生叫梅一清,在某唐樓的一角,開業多年,診所頗舊,醫術高明之餘,人也較隨和。也許因其名字關係,許多性病人上門求診,最後索性由胸肺專科改為梅毒專科,本人未有幸染此頑疾,所以未有再找梅醫師求診了。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