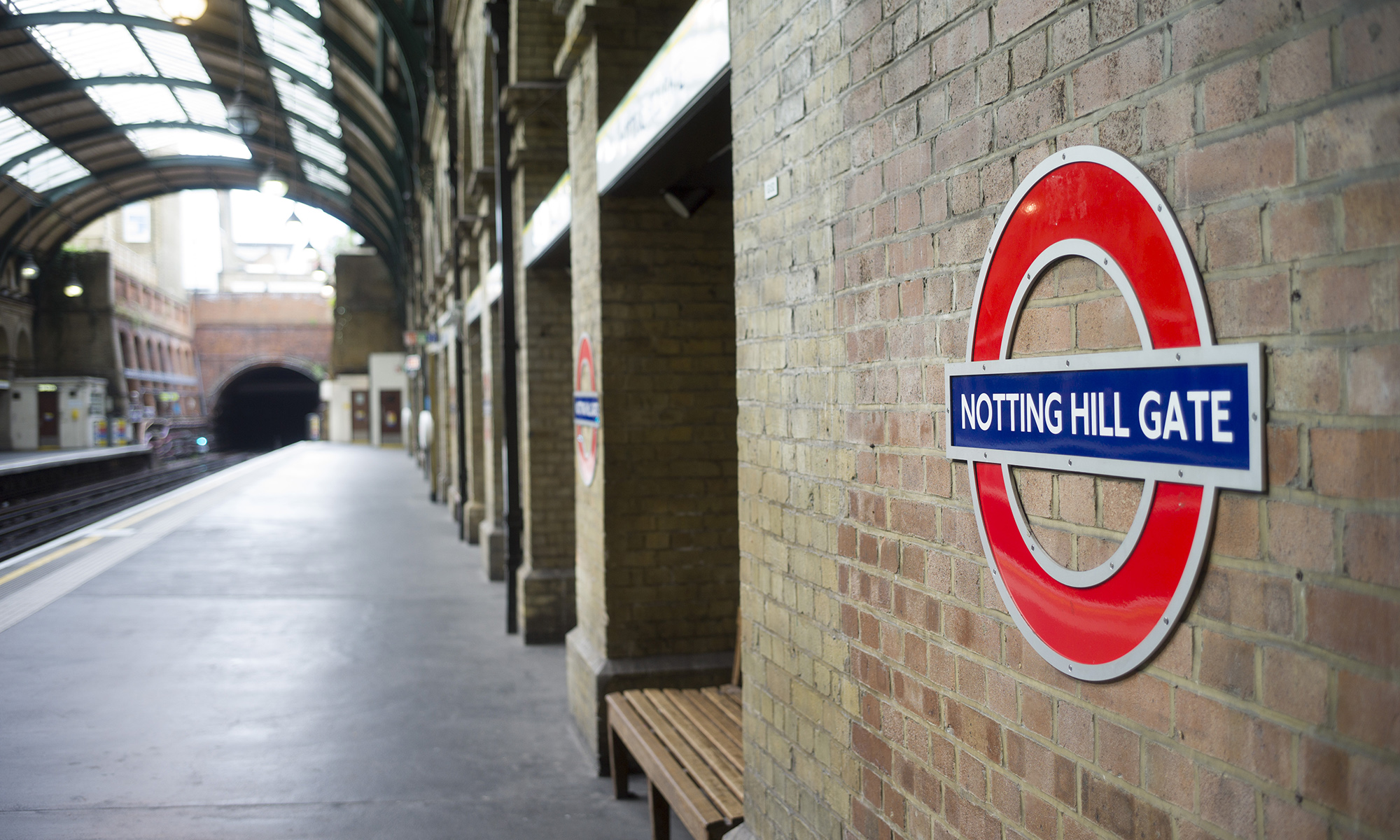朋友說要給我介紹一位女伴,並說她個性比較『傳統』,意思是她熱愛中國習俗及文化。聽罷,童心一起,考了她兩個關於中國節日的問題:
- 中國節日中,有哪兩個節日是依太陽曆法1來推算的?
- 農曆單數重數的日子都有一個特定的節日,例如一月一日、三月三日2、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及九月九日等等,當中有沒有玄機?
第一條問題比較容易,反而是太陽曆及月亮曆的既念比較陌生,但朋友是外國人,農曆一詞英語譯作 Lunar Calendar,就是月亮曆的意思,他反比一般香港人更明白這個既念。節日依太陽曆法來推算,簡單一點說,就是這個節日每年都在西曆的同一日出現,而非農曆,原因西曆是依太陽曆法計算的。這兩個節日是清明節及冬節,尤其是冬節,為一年中日照最長、黑夜最短的日子,意思是經過這一天後,大地將逐步趨向復甦,這種天文現象跟地球圍繞著太陽公轉有關,當然要依太陽曆推算。
第二條問題其實沒有答案,原因內地學者並沒有對這個現象作過深入研究,只有日本學者池田溫曾經發表過一篇較有份量論文而已,但論文並沒有對該現象作出結論,我們只能歸咎於巧合,或當時朝廷對節日的規範。值得一提的是上巳節﹝三月三日﹞,是古代舉行「祓除畔浴」的節日,即是集體淋浴的日子。宋代以後,中國人漸趨保守,集體沖涼這樣大逆不道的事,當然要步向式微了。然而,日本的女兒節及東南亞地區的潑水節仍然遺留著當留年上巳節的影子。
說罷,我轉頭問朋友:『三月三日,她會不會跟我一起「祓除畔浴」?』朋友瞪了我一眼,並謂以後不再跟我介紹女朋友云云。
- 太陽曆:http://zh.wikipedia.org/zh-hk/%E9%98%B3%E5%8E%86
- 上巳節: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8%8A%E5%B7%B3%E8%8A%82
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