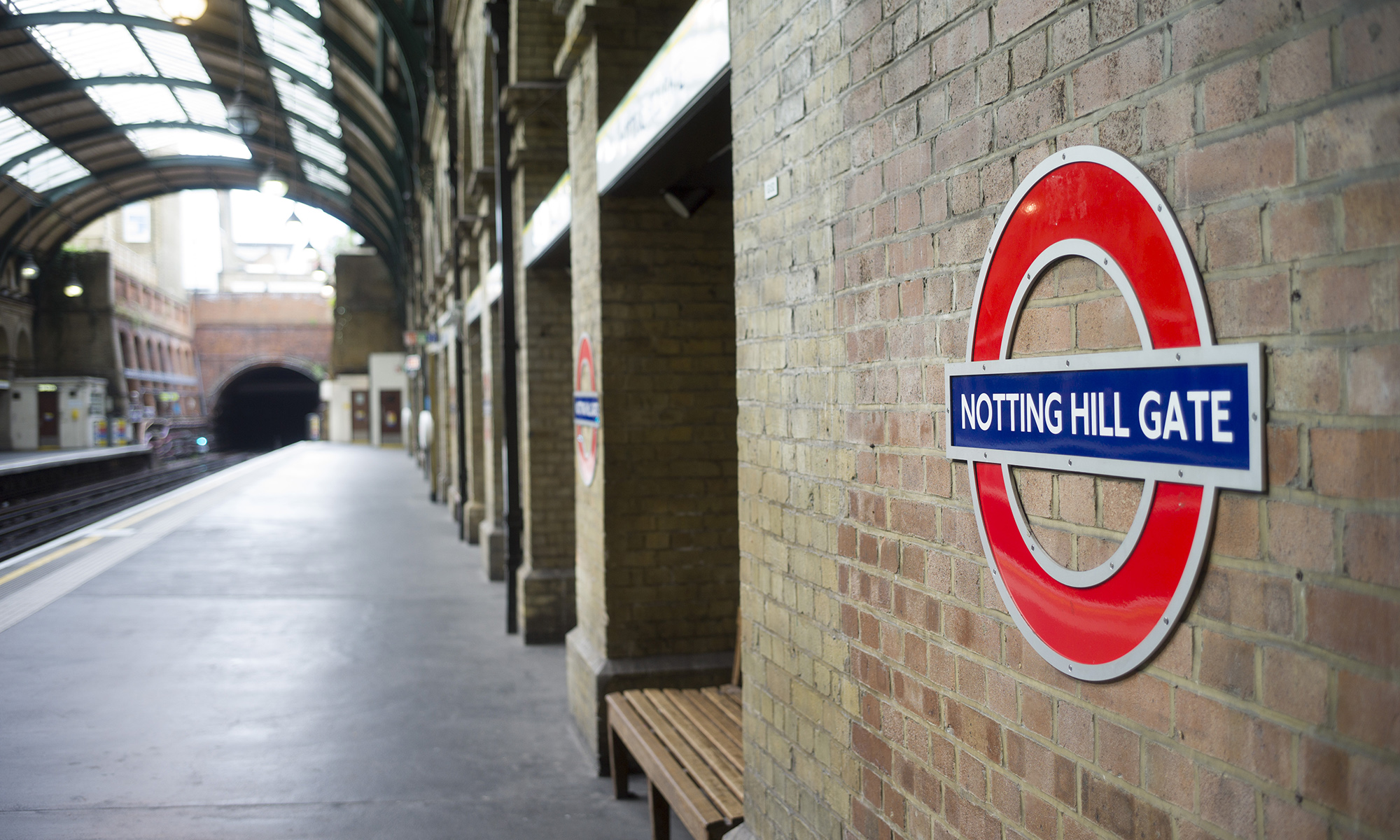記得在圖書館學院入學面試時,系主任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要修讀圖書館學?當時我已經擁有一個電腦碩士學位,並在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上班。我說:因為我想幹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系主任覺得我的選擇匪夷所思。幾年後,在文學院入學面試時,院長也問了我相同的問題,為什麼要來修讀中文?當時我的職位已經是高級館長,看來是不會『轉行』了。我說:書讀了三十年,我想修讀一些自己喜歡的科目,系主任仍然覺得我的選擇匪夷所思。事實上,往後兩年面對著學費單時,我同樣覺得自己的選擇匪夷所思。
對中文的興趣,或許源自王德威教授的『原鄉想像』,他認為海外浪人都會追逐原鄉夢想。小弟旅居海外十多年,中國文化跟相隔異地的戀人一樣,愈是若即若離,愈要感到興趣。但愈感到興趣,卻愈覺得疑惑,文化本身有許多規條,拜年、紅包、月餅、湯丸、登高等等,但從來沒有人去了解過前因後果。後來才知道,原來中國人對文化的承傳,一代接一代的承襲下來,是從來不會去問原因的。舉例說,當我上第一課研究院的中文課時,鄧仕樑教授問了一個家傳戶曉的問題:為什麼唐詩最具藝術價值?幾十年來,只有人告訴我唐詩最具藝術價值,但從來沒有人來解釋過箇中的原因。
記得中學時期,倪匡先生的小說一紙風行,許多都賣至斷版。母親在家長會上曾要求班主任向我勸說少看點閒書,誰不知,那時候老師正向我借了《老貓》及《大廈》兩部小說。除了倪匡的科幻小說,還有亦舒、古龍、金庸等作品亦非常流行。也許我比較保守,總覺得文字的魅力在於含蓄,給讀者留有幻想空間,但現代人的腦袋卻愈來愈懶,『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那及得上《赤壁》上的浩大視覺場面?不知道是否已經跟現代人出現了代溝,現代人對文字的追求己經不可同日而語。再寫手記之後,朋友第一句評語是:不看沒圖片的東西;在科林上發表了一篇沒口語的白話文字,竟然被評說在寫『古文』。
對了,為什麼唐詩最具藝術價值?鄧教授當時沒說明,或者答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直至畢業後,才發覺問題本身已經存在弔詭之處:『藝術』是西方美學的定義,以西方美學觀點去評價唐詩,雖然不是新鮮題材,但足夠發揮成一篇論文了。
406